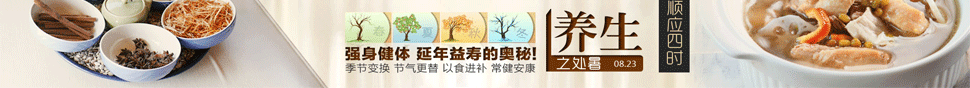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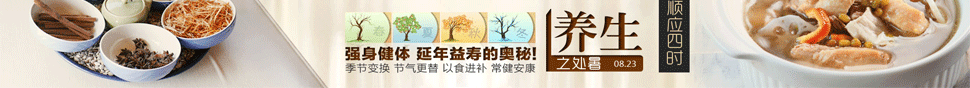
●
董作宾在李庄时期的
甲骨文研究与书法创作
︱刘振宇︱
甲骨文是商代至周初之际锲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有科学体系的文字。年王懿荣的甲骨文发现,揭开了殷商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和甲骨文书法创作的序幕。一百多年来,名家辈出,论作如林,精彩纷呈,其中尤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郭沫若《卜辞通纂》、董作宾《殷历谱》备受学界称颂,堪称凿破鸿蒙的学术经典。四大名著中,《殷历谱》写作最为曲折、耗时最长、费力最多。
董作宾像
年4月30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董作宾编写的《殷历谱》在四川宜宾李庄以手写石印方式诞生。这部里程碑式的学术巨著一出版,就获得学术界的广泛好评,马衡、李济、唐兰、朱自清、郭沫若、徐炳旭等著名学者纷纷致函道贺,胡适先生认为“彦堂这部书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境界”。以严谨谦逊著称的陈寅恪先生也赞誉有加,认为“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
接受完国民党政府的嘉勉,董作宾一如平常的淡然,白天处理史语所的行政工作,晚上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这样的生活,已经坚持了17年。自年专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来,董作宾先生就与甲骨文结下了美妙之缘。他亲赴殷墟,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得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的结论,促成了中央研究院对殷墟长达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科学发掘。年10月,他又主持殷墟第一次发掘工作,获有字甲骨片及其他器物多件。从年10月至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对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董作宾是第一、五、七、九四次发掘的主持人,第二、三、四、六四次发掘的参加者,并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委托监察第十一、十三两次的发掘。年发表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董作宾首次在甲骨卜辞中发现“贞人”之名,并提出了分期断代的八项标准。年又发表了著名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分期断代的十项标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法),并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五期,建立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学说。把甲骨学研究纳入历史考古范畴,从而使甲骨学由金石学的附庸,转化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建立了甲骨学的科学研究体系,将甲骨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科学阶段。
董作宾故居一景
《殷历谱》的写作是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升华,从年开始,到年在李庄正式完稿,前后历时十年,数易其稿。目睹写作历程的傅斯年深知其艰辛,在该书序言中说:“殷历谱者,吾友董彦堂先生积十年之力而成之书也。彦堂天资高迈,精力过人。十载兵戈,漂泊于西南天地之间,此谱耗其岁月约三分之一,若四之一。然彦堂一人每日可为之事当常人三四,故若他人为之,即才力相若,不窥园亭,抑或须一纪,此其所以使友朋辈无不羡妒者也。手写太半,征序于余。余于古历法与甲骨文字皆未有入门之功,何敢置辞?虽然彦堂之治甲骨学将二十年,此将二十年之月日,皆与余共事中央研究院,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进一步,即是彦堂之每进一步。”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四卷:一、殷历鸟瞰,二、历谱之编制,三、祀与年,四、殷之年代。下编十卷:一、年历谱,二、祀谱,三、交食谱,四、日至谱,五、闰谱,六、朔谱,七、月谱,八、旬谱,九、日谱,十、夕谱。
董作宾甲骨卜辞纸本墨笔
纵72厘米横31厘米年
成都市博物馆藏
关于编写目的,董作宾在自序中说:“此书虽名殷历谱,实则应用断代研究更近一步之方法,试作甲骨文字分期、分类、分派研究之书也。余之目的一为藉卜辞中有关天文历法之记录,以解决殷周年代之问题。一为揭示用新法研究甲骨文字之结果,以供治斯学者之参考,前者在历,后者在谱,盖由谱以证历,非屈历以就谱。”在研究殷商历法的过程中,董作宾广泛应用西方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记录检验殷商古代历法,澄清了商朝统治时期的继位顺序,考订了殷商的实际统治年数及周灭商的确切年代,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历法表收集整理分类了各种特定时期给祖先和其他神灵供奉牺牲的记录,揭示了祭祀仪式的内容与实质。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李济博士在阅读完《殷历谱》后高度评价董作宾的工作,认为“其目的是用科学分析把数量惊人的甲骨材料和现代日期联系起来,为此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化成就的代表”。
董作宾先生在殷商甲骨分期断代方面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研究,使之成为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一代宗师,与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并称“甲骨四堂”(董作宾字彦堂)。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甲骨文书法大家,是民国学者书法的代表性人物。清末民初,帖学极盛而衰,每况愈下。康有为《广艺舟双辑》的“崇碑抑帖,尊魏卑唐”之论,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却振聋发聩,震撼人心,一时碑学大兴,几乎独霸书坛,以取法六朝金石铭刻为主,但也有以二王为宗,以帖入碑,碑帖熔冶兼容并蓄的,碑帖之争,此起彼伏。而甲骨文的发现石破天惊,在改写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同时,也为汉字书法创作开辟了一个全新领域。罗振玉编印的《集殷墟文字楹联》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甲骨文书法作品集,开创了以甲骨文可释文字集字进行书法创作的风气。继罗氏之后,涌现出章钰、丁辅之、马衡、简琴斋、叶玉森、容庚、商承祚等一批甲骨文书法家。面对三千年前的古文字,不仅考释困难,要进行书法创作更是困难。这就要求书写者不仅要有高超的书写技巧,更需有渊博的学识,对甲骨文字义、用法有深刻的理解。董作宾能涉足古人所无的甲骨文,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且能将其引向深化,形成海内皆知的董派甲骨文书法,更是难能可贵。董作宾先生能在甲骨文书法上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全赖其博大精深的学识和长期的整理摹写工作。
董作宾因整理研究殷墟出土甲骨文的需要,与甲骨卜辞原刻朝夕相处,加之擅长篆刻,喜好书画,故对甲骨文书法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甲骨文,在20世纪初叶,曾为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放了一个异彩,它的光芒四射,炫耀全世界。同时,它的一条光线支流,表现于书法美术。我们中国的文字,三千年前,在殷代,已由图变成了符号,这种符号,完全用线条书写,这种线条有刚健柔媚各种不同的姿态,尤其在一些象形字中,很接近大写意的原始图画,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美观。甲骨文本身,有过约二百七十三年的历史,它的书契,有肥,有瘦,有方,有圆,或是劲峭刚健,有顽廉儒立的精神;或是婀娜多姿,有潇洒飘逸的感觉。举殷代中兴名王武丁时代为例,那时候的史臣们书契文字,气魄宏放,技术娴练,字里行间,充满了艺术的自由精神,决不是其余各王朝所能比拟的。所以我也喜欢写这一派”。
董作宾朱书甲骨卜辞纸本墨笔
纵93厘米横33厘米年
成都市博物馆藏
对于董作宾临习甲骨文书法的历程,曾跟随董老从事安阳殷墟发掘的石璋如院士回忆说:“董先生认为研究甲骨,摹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先用玻璃纸蒙在拓片上,勾出轮廓,再与原版甲骨对照着摹写其上的卜辞。董先生觉得对着原版甲骨摹写了一遍才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董先生能精于甲骨文书法,这个摹写的工作的确又给他一个训练的机会。董先生喜欢书写甲骨文对联,年前后,便有相当兴趣,不过在那个时候写的东西并不多,年到昆明龙兴村之后,每于公余之暇,借写甲骨文对联以自娱,并临摹殷墟文字精华成条幅、横披等。在初书阶段,兴趣极高,常把写好的东西送给来访的朋友,后来能成为甲骨文书法名家,就是在龙兴村时打下的好根基。”搬到李庄后,因为《殷历谱》写作的需要,董作宾于甲骨文书法更是不遗余力。
董作宾先生对于殷商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心摹手追,行笔书写时如对神明,用笔如刀,下笔果断,起笔藏锋,收笔出锋,笔致秀朗,端丽典雅,骨肉停匀,转折舒徐,神定气盛,无任何枯燥迟涩的现象,既有很好的笔墨趣味,又保留了甲骨文犀利劲峭的锲刻特点,将殷商武丁时期甲骨卜辞笔画的遒丽挺拔、姿态的圆润婀娜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罗振玉用小篆之法书写甲骨文截然不同,罗氏甲骨文书法是吸收篆意雅化,起笔藏锋,间用侧锋,虽笔画圆泽、隽雅质朴,但却改变了甲骨原刻恣肆放纵、劲峭挺拔之风。而叶玉森则太过于追求刀刻效果,虽挺拔明快、宛转舒徐,但不免在用笔上给人雷同之感。董作宾先生所书甲骨卜辞在章法布白上得甲骨原刻参差错落、自然生成之神韵,对联大字布局匀称,疏密得体,刚劲壮丽,凛凛英姿,浑然天成,扇面小字,灵活飞动,契意浓郁,令人爱不释手。金石学家罗伯希、萧友于、杨叔子得知中央研究院搬迁到李庄后,都不愿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纷纷前往请教,并以得到甲骨文墨宝为幸事,由于董作宾先生为人大度,有求必应,一时“宜宾纸贵”。
董作宾留别李庄栗峰碑铭拓片
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藏
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代学术精英以其超迈卓绝的胸襟,自愿将守护中国文化根性的重任肩负起来,探索新领域、构建新学科,董作宾与傅斯年、李济、陶孟和、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凌纯声等在李庄居住了五六年,虽然为时不长,但这段不同寻常的日子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可谓刻骨铭心。那些完成于李庄的人文著述,如董作宾的《殷历谱》、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李霖灿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使边远的李庄古镇声名鹊起。如今,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段恢宏历程的过往细节竟如昨日花香,开始变得缥缈难辨,然而往事并不如烟,虔诚的后来者不远千里来到古镇,透过木质的旧门、残损的窗棂、曲折的老街,挥霍无尽的遐思,寻求精神的皈依。
作者就职于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四川管理处
(编辑:张楠)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期︱
图文版权所有,如需转载,务必注明出处!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